女大學(xué)生賣身救母【“墮落”的政法系女大學(xué)生舍身救母】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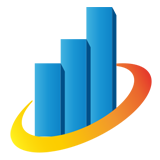 2023-01-16 04:15:32財(cái)都小生
2023-01-16 04:15:32財(cái)都小生林語(yǔ)嫣身著暴露的吊帶裙,目光呆滯地站在了聳入云天的“深江”賓館頂樓。此刻,她只想縱身一躍而下,輕然地和那些漫天飛舞的落花一起靜靜地融為塵泥。
闌珊的夜色在城市霓虹燈奇幻的潑染下,愈發(fā)顯得狐媚與煽情。想到悲情處,洶涌而至的淚水便開始順著她清瘦﹑憂傷的臉頰,肆意地向著潮濕、陰冷的空中不斷地飄飛著。如果用那些晶瑩無(wú)暇,冰純至極的淚水,能夠沖洗去業(yè)已深入進(jìn)她靈魂深處的“齷齪”,她愿意流盡生命中的最后一滴眼淚……
林語(yǔ)嫣原本是“漢南”政法系大三的高材生,也是唯一一個(gè)從當(dāng)?shù)貥O度赤貧的深山溝里幸運(yùn)地跳出“農(nóng)門”的女大學(xué)生。20歲的林語(yǔ)嫣自幼便和孀居了近10年的寡母一起嘗盡了苦難人生中的那些大悲大痛。如果說(shuō)以往的生活是一本波瀾壯闊的“歷史書”,那么這本書必定悲情地融入了她和母親的萬(wàn)千血淚,融入進(jìn)了她無(wú)盡的﹑巨大的悲哀。
記得她考入“漢南大學(xué)”的那年,母親厚著老臉,拖著病懨懨的身體,挨家挨戶地去向村里人借錢,以便湊足她上學(xué)的路資和學(xué)費(fèi)。但凡家里能夠拿來(lái)?yè)Q錢的家什,早已經(jīng)被母親“掃蕩一空”,拿去集市上賤賣了。什么叫家徒四壁,什么叫欲哭無(wú)淚,想必只有過(guò)早地經(jīng)歷了人世間萬(wàn)般苦難的林語(yǔ)嫣,心里最為清楚明了。
十里山路,蜿蜒起伏地橫亙?cè)跍嫔F鄾龅幕钠麻g,林語(yǔ)嫣淚流滿面地目送著母親佝僂﹑病弱的身影,漸而漸的消失在了蒼茫﹑氤氳的山坳里,她的心不由得一陣陣劇痛,那些觸及肺腑的灼灼淚水,便開始在她冰寒的世界里,汪洋恣肆了……
母親的身體每況愈下,整日整夜間咳嗽個(gè)不停,但她還強(qiáng)撐著羸弱的身體,忙于田間地頭,耕作在烈日和暴風(fēng)雨下。林語(yǔ)嫣深知母親的病多半是因過(guò)度勞累而誘發(fā)的。這些年來(lái),煢煢孑立的母親活得悲天憐人,萬(wàn)分艱難,為了能夠盡快還清外債,母親在“閑暇”的時(shí)候,竟背著她偷偷地跑去大山深處的采石場(chǎng)背運(yùn)石頭。
林語(yǔ)嫣曾因此而大聲地“呵責(zé)”過(guò)母親,也曾以“斷絕”母女關(guān)系的“幌子”來(lái)“要挾”過(guò)母親,但每每母親總是報(bào)以“羞澀”的一笑,依然我行我素。對(duì)于女兒的苦心規(guī)勸,她總是“置若罔聞”。母親的心,只有她最懂,她不想在有生之年拖累了女兒,更不想讓心無(wú)旁騖﹑一心讀書的女兒,為清貧的生活而憂思焦慮。
林語(yǔ)嫣在進(jìn)入漢南大學(xué)讀書的時(shí)候,就成功地爭(zhēng)取到了學(xué)校的全額獎(jiǎng)學(xué)金,應(yīng)對(duì)簡(jiǎn)單的生活開支,倒是能夠勉強(qiáng)過(guò)得去。她將每日硬生生地從牙縫里摳儉下來(lái)的那些零碎的錢,一分一毫地?cái)€起來(lái)給母親買一些營(yíng)養(yǎng)品或者小點(diǎn)心之類,拿來(lái)孝敬母親。
母親常常佯裝生氣地對(duì)她“溫柔”地“說(shuō)落”著——不要再為她而花費(fèi)那些“冤枉錢”。在學(xué)校得穿得體面一些,要為自己置辦件像樣的衣服,不能總像大山溝里的村民一般,整日不修“邊幅”,穿得“邋邋遢遢”的,哪還像個(gè)大學(xué)生的樣兒?林語(yǔ)嫣常常一臉幸福地“享受”著母親的這種“說(shuō)教”,這種被母親“千嬌萬(wàn)寵”的感覺(jué),真好。
在林語(yǔ)嫣上大三的那年秋天,禍從天降--她母親徹徹底底得病倒了,母親像蝦米一般痛苦不堪地蜷縮在那張窄小的床榻上,從胸腔中呼出的顫音如同灶臺(tái)下拉響的風(fēng)箱一般得異常沉悶,更為糟糕的是母親的唾液中竟然摻雜著腥紅的斑斑血跡。林語(yǔ)嫣聞?dòng)嵑螅f(wàn)分驚恐,她沒(méi)來(lái)得及向?qū)熣?qǐng)假,便萬(wàn)分悲痛﹑十萬(wàn)火急地直往家里趕……
母親極力地“阻擾”著女兒帶她去省城醫(yī)院看病,她知道住一次醫(yī)院,將要花去她多年來(lái)辛苦積攢下來(lái)的那部分“可憐”的積蓄。這些錢原本是拿來(lái)償還外債的,她始終不忍將那筆看做比自己命根子還要重要的積蓄,無(wú)緣無(wú)故地在醫(yī)院打了“水漂”。她寧愿在家里“負(fù)隅頑抗”,也不愿意去醫(yī)院活生生地遭受那份“洋罪”。
林語(yǔ)嫣悲痛萬(wàn)分﹑淚流滿面地跪在了母親的床前,聲嘶力竭地苦苦哀求著母親和她一起去省城醫(yī)院做進(jìn)一步的檢查,哪怕母親不住院,只“簡(jiǎn)單”地診斷一下病因,開幾副藥回家服用也是好的,起碼可以讓她狂亂不已的心,能夠稍漸安穩(wěn)一些。母親淚眼婆娑地看著近乎絕望的女兒,最后勉為其難地點(diǎn)了點(diǎn)頭……
蒼天無(wú)淚,驚雷至天邊滾滾而起。當(dāng)身心俱疲的林語(yǔ)嫣哆哆嗦嗦地拿著母親的一紙確診書,她徹底地崩潰了——“肺癌晚期”,這四個(gè)在她眼前似乎被放大了億萬(wàn)倍的“假想”字,在林語(yǔ)嫣的眸前不斷地晃來(lái)蕩去,她近乎絕望地扶著醫(yī)院那面冰冷的墻壁,舉步維艱地向著母親的病房哆哆嗦嗦地走去。
心內(nèi)科的廖主任直言不諱地告訴林語(yǔ)嫣,以她母親現(xiàn)在的這一身體狀況,并不適合于做放﹑化療,當(dāng)前她母親最為穩(wěn)妥的治療方案是保守治療,長(zhǎng)期服用一種靶向藥——阿法替尼,可以在一定時(shí)間段內(nèi)有效抑制癌細(xì)胞的侵襲,但這個(gè)藥得自費(fèi),而且價(jià)格不菲……
“語(yǔ)嫣,媽的病還有救嗎?”母親悲滄地看著一臉憂郁的女兒,哽咽地向她詢問(wèn)道。“媽,醫(yī)生說(shuō),您的病并不打緊,您就是患上了慢性支氣管炎,您咳嗽的時(shí)候,不小心撕裂了聲帶,服用幾劑云南白藥就可以止血……”林語(yǔ)嫣背對(duì)著母親,一任那些洶涌澎湃的眼淚,肆意地從她悲深的眼眶中歡快地流淌了下來(lái)。它們終究要流向何方?哪兒才是它們?nèi)~落歸根的家?
林語(yǔ)嫣披頭散發(fā)﹑失魂落魄地行走在熙熙攘攘﹑人語(yǔ)喧闐的中山南二路。往日,她會(huì)偶爾“趁閑”,怯怯地放緩腳步,略帶憂傷地來(lái)“感觀”一下這個(gè)城市絢爛多彩的“奢靡”生活。但是自從她踏入這個(gè)城市的那一刻起,她就“卑微”地認(rèn)為,她和這個(gè)城市之間實(shí)則相隔萬(wàn)里之遙。她只是“寄居”在這個(gè)陌生﹑冰冷城市的一名“熟悉”的“租客”而已,一個(gè)流浪在這個(gè)城市邊緣的“乞兒”。
凄冷的夜風(fēng),為她不斷地擦拭去漫出眸宇間的那些咸澀的淚水,城市虛幻的霓虹燈和潛在詭異燈影下的那些不安分的身影,似乎在向她“魅惑”地頻頻招著手,她竟鬼使神差般得向著那道為她而敞開的“地獄門”,淚流滿面地走去……
林語(yǔ)嫣“被迫”輟學(xué)了,曾經(jīng)那個(gè)品學(xué)兼優(yōu)的政法系的女高材生,曾經(jīng)那個(gè)憂傷地徘徊在漢南大學(xué),腹有詩(shī)書氣自華的花季少女,最后“自甘墮落”地淪為了一種待價(jià)而沽的“商品”。
一切都是她言不由衷得“任性”選擇,似乎和命運(yùn)有關(guān),似乎又沒(méi)有什么本質(zhì)上的聯(lián)系。這一切都是她“咎由自取”的,但她不會(huì)因此而怨恨“無(wú)能”的上帝,也不會(huì)怨責(zé)身患重病的母親。如果這一切都能夠重新來(lái)過(guò),也無(wú)法撼動(dòng)她“賣身救母”的決心和勇氣。母親是她生命中的唯一,也是她生命中的全部?jī)?nèi)容,她不想因?yàn)樽约翰回?fù)責(zé)任的有意逃避,而抱憾終身。
林語(yǔ)嫣顫抖著重新燃上了一根煙,隨著裊裊升騰的煙霧,她焦狂的內(nèi)心漸漸地平復(fù)了下來(lái)。此刻,她迫切地想要把母親接到北京﹑上海的那些最頂級(jí)的腫瘤醫(yī)院去治療,只要母親的病情能夠逐步地穩(wěn)定下來(lái),那么就讓她因此而形神俱滅﹑挫骨揚(yáng)灰,她也毫無(wú)怨言。
林語(yǔ)嫣默默地擦去了掛在腮前的那一竄冰純無(wú)暇的淚花兒,步履維艱地從“深江”賓館的頂樓失魂落魄地走下來(lái),然后在洗漱室換了一套印有“漢南大學(xué)”字樣的校裝,便行色匆匆地往省立醫(yī)院趕去。此刻,她想著焦灼萬(wàn)分的母親,似乎正在慌亂地等著她的歸來(lái)……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