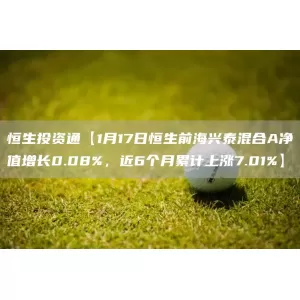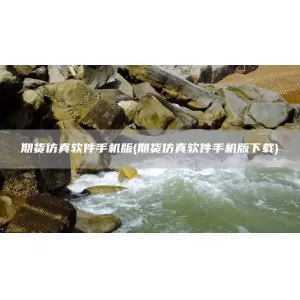富士康4天2跳【華為的未來】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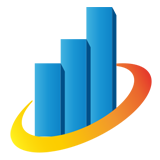 2023-01-10 03:15:18財都小生
2023-01-10 03:15:18財都小生——富士康銷售語錄
01 路口
2009年,郭臺銘春風得意。
雖然世界經濟危機讓富士康斷了連續30%的增長勢頭,但14.2%的數據,還是能讓他在股東大會上輕松笑談:
抱歉,賺的沒有預期的多。
郭臺銘在股東大會上
確實,在全球一片哀鴻遍野的時刻,這種逆風上揚的能力更讓人踏實。尤其近來最閃耀的明星、年增36%的華為,已經將訂單送到了富士康手中,讓郭臺銘對未來充滿信心:
過去二十年,富士康是“中國制造”的代言人;今天的富士康,有能力成為未來“中國創造”的最佳代言者。
這一番振奮人心的演講,題目為《黃金十年,贏在大陸》,是郭臺銘自己取的。
同年,18歲的河南小伙馬向前南下千里,入職深圳富士康觀瀾廠區。
幾個月后,他被人發現躺在了工廠宿舍的樓梯口。最終,警方的調查結果是“生前高墜死亡”。
讓人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是,馬向前的死亡如同開啟了潘多拉魔盒,此后便是震驚社會的“富士康13連跳”,讓郭臺銘瞬間從陽春進入寒冬。
盡享大陸20年人口紅利的富士康,就這樣猝然走到了十字路口。而之前10年狂飆突進的“中國制造”,也由此迎來了下半場考驗。
02 深圳
網絡搜索馬向前,首條結果是“深圳富士康猝死員工”。但關于他本人的介紹,卻僅有“河南”、“19歲”兩個注解,其生前經歷更是空白一片。
2010年,富士康在職員工人數突破90萬。如果這是一支軍隊,郭臺銘就是掌握全球第六大軍事力量的統帥。
所以,90萬中的普通一兵,理所當然的不會在時代留下痕跡。除非,他是媒體口中的“13連跳之第1跳”。
相比之下,“統帥”的履歷則是詳盡之極:1950年出生于臺灣省,祖籍山西晉城。1974年創業,以模具和連接器起家。1985年,創立富士康品牌。1988年,入住深圳,自此開啟了帝國的隆隆征程。
1988年初到深圳的郭臺銘
有趣的是,這一年5月的《深圳特區報》刊登了一篇名為《充滿活力的一株幼苗》的報道,任正非三個字首次出現在了公眾視野。
即便20年后郭臺銘與任正非才首次相見,他們卻默契的共同選擇了深圳這座站在潮頭的城市,撐起最初的征程。
03 民工
90年代的深圳,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口號:
來了就是深圳人。
在如今的語境中,似乎當年聽從召喚的先行者都已成了千萬富翁。成長期的深圳被描繪成舉目皆財之地,“隨便買套房、做個小生意,現在就是妥妥的財富自由”。
90年代初的深圳年輕人
可是,剛剛擺脫貧瘠的國人哪有這等眼光與膽量。千里南來者,追夢者寥寥,所求不過一個不看老天眼色的安穩。
后來,他們有了一個共同的名字,“農民工”。
至于2009年來到深圳的馬向前有沒有夢想,又有誰知?
而此時的郭臺銘,面對海峽兩岸2000塊的月工資差價和洶涌而來的民工大軍,站在龍華興奮的說:“這一片地,我都要了”。
多年后的富士康深圳龍華園區
同年,富士康將世界級大廠Compaq、Intel、Dell的訂單收入囊中,靠的就是文章開頭的那句話:
你自己做,不如我做便宜。你讓別人做,也不如我做便宜。
04 爭奪
2001年,郭臺銘品嘗到了臺灣民營制造業第一的滋味。
既然深圳一地就能制霸一省,那布局全國又當如何?
富士康在深圳的第二個園區:觀瀾
另一邊,自帶就業、稅收、消費光環的富士康,也成為各個地方的心頭好。2003年,杭州錢塘科技園落成。2004年,太原科技園一期落成。同年,煙臺科技園開工。2005年,武漢與富士康達成協議。2006年,河北秦皇島科技園敲定。
以上諸地能在如火如荼的“富士康爭奪戰”中脫穎而出,既有政策、環境的硬功夫,也有以情動人的小心思。
例如太原項目,就是在郭臺銘回鄉祭祖時拿下的。據說他當場以“晉商”自居,言稱一直奉拜關公。
回鄉的郭臺銘迎“關公”
至于20年后怎么又信了媽祖,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了。
山西打出了“祖籍”牌,山東也特意找到郭臺銘母親當年的故居,整修一新。煙臺科技園隨即開工,老太太還順手在當地捐了一座中學。
郭臺銘與母親出席捐贈中學儀式
武漢則花30萬制作了一部專題片,以“山水兆富、環境納士、佛嶺蘊康”開題,讓郭臺銘贊不絕口。
在那個剛剛擠進WTO、初登世界舞臺的歲月,誰能擁有一座富士康廠,就相當于抄了國際化的捷徑。
05 八卦
那些年,富士康背靠大陸賺的盆滿缽滿。但相比統一、旺旺等耳熟能詳的臺灣品牌,富士康一直低調的隱身于公共視線之外。直到2006年,《第一財經日報》發表了一篇名為《富士康員工:機器罰你站12小時》的報道,“血汗工廠”一詞第一次見諸報端。
郭臺銘大怒,索賠3000萬。
不曾想,這一舉動直接將全國媒體推到了對立面,一時間口誅筆伐鋪天蓋地,山雨欲來。
眼見勢頭不妙,富士康立刻將索賠數從3000萬降至1元,后來干脆撤了訴,風波就此平息。吊詭的是,熱鬧的官司吸引了全部視線,報道反映的問題卻沒人重視。
此時距離震驚全國的“13連跳”,還有4年。
更諷刺的是,郭臺銘三個字開始頻繁出現在娛樂版塊。2005年發妻林淑如去世后,這位臺灣首富的私生活就成了八卦媒體的焦點,無論是林志玲還是劉嘉玲,都妥妥占據娛樂頭版。
那時的吃瓜群眾分不清富士康和康師傅,卻不妨礙對“郭劉梁三角戀”喜聞樂見。
最終,先吃了螃蟹的還是外國媒體。2007年,《華爾街日報》走進深圳龍華,打開了從未對外的制造帝國:
這里的工人24小時倒班工作,工資按發達國家標準少的可憐,卻足以招募到一批又一批的新工人。
這是郭臺銘的“紫禁城”。
06 連跳
10年前,我還在某網站做編輯,那一年的5月讓人心悸。
印象中,幾乎每天晨會總編都會說:“跟一下富士康,又跳了。”
接連而至的負面消息,讓編輯部的氣氛變得壓抑沉重。而身處旋渦中心的郭臺銘更是幾近崩潰。
如果說1月23日馬向前的“第1跳”還未引起波瀾,那從3月11日至5月11日的7連跳,已經讓郭臺銘亂了方寸,甚至想請五臺山高僧做法“破解”。
然而,之后的11天里,8、9、10跳還是接連而至,砸在人們的心上。
5月26日,郭臺銘連夜趕回深圳。下飛機時,他嘴唇顫抖著說:
我現在最怕晚上11點接到電話。
當晚11點,第11跳,一語成讖。僅僅幾個小時后的27日凌晨,第12跳。
第二天,郭臺銘向眾多媒體一躬到地:
對不起。
郭臺銘道歉
6月,富士康用瘋狂加薪按下了“連跳暫停鍵”;等待入職的年輕人,依然在龍華園區外排起長龍。
擁擠成一團的等待面試的人群
郭臺銘想不明白,為什么富士康薪資高、不拖欠,員工還要跳樓?
同月,蘋果推出神作iphone4。喬布斯在發布會上說的那句“再一次改變一切”,至今仍被無數果粉懷念。
其實,這句話也恰恰是富士康癥結所在。
一成不變的廠房、宿舍、食堂,一成不變的重復、枯燥、麻木,一復一日,年復一年。沒有一絲一毫的改變,沒有一絲一毫的希望。
他們逃避了田間地頭的風吹日曬,也失去了朝陽晚霞、蟲鳴蛙叫;他們化身《摩登時代》里的螺絲釘,被死死擰在了流水線上;他們親手造出了“改變一切”的iphone,卻改變不了自己的人生。
郭臺銘不明白這些。
或者,他明白,他卻無法改變。
2010年8月,深圳富士康舉辦大型聯誼活動
07 假設
改變不了員工命運的郭臺銘,決定改變選址策略。
北上,西進。
2010年年底,郭臺銘來到了馬向前的老家,河南。“13連跳”的陰影下,原來的“爭奪大軍”踟躕不前,只有河南熱情依舊。
郭臺銘在河南
對于富士康而言,這個職業教育發達的勞動力大省,正合胃口。
最終,一個面積是龍華4倍的廠區落戶鄭州。一個月后,一期廠房拔地而起,讓郭臺銘切切實實的領教了一把“鄭州速度”。
不過,之后的幾年卻是富士康帶著鄭州一飛沖天。新鄭保稅區獲批,中興、OPPO接連入駐,鄭東新城終于煥發了活力。
另一邊,越來越多的河南人在家門口找到了工作。
鄭州富士康
毫無疑問,這是一個完美的雙贏選擇。
可是,假如富士康早一年來到鄭州,馬向前還會去深圳嗎?還會跳樓嗎?“13連跳”的悲劇還會上演嗎?
歷史,總是經不起半點假設。
08 錯判
鄭州的成功,讓郭臺銘開啟了新一個十年的跑馬圈地:貴州、廣西、山西晉城、山東菏澤…牢牢遵循著向西、向北的原則。
富士康不完全分布圖
2011年,去世前的喬布斯做了兩件事。一是力挺郭臺銘,不僅自掏腰包將美國心理專家派到龍華,更返還了2%的利潤用來提高富士康員工工資;二是堅定的告訴奧巴馬:
那些工作回不來了。
另一邊,在東南亞、巴西轉了一圈的郭臺銘比喬布斯更加篤定:制造業不僅回不了美國,更出不了中國。
巴西富士康
再沒有一個地方的人民,能這般拼命。
就這樣,郭臺銘左手拽著大陸二三線人口紅利,右手拽著蘋果,再次騰飛。
一場危機卻在2017年悄然到來。
客觀來說,大陸人口紅利的消退、蘋果的萎靡,是無法回避的危機根源。但郭臺銘在方向上的一系列錯判,無疑才是衰退的導火索。
特朗普上臺后,把一向精明的郭臺銘忽悠“瘸了”。先是拒絕了華為的代工訂單,后又馬不停蹄的奔赴美國、印度設廠,要與蘋果深度捆綁。
沒想到庫克和喬老爺態度如出一轍:“回歸美國?不可能”。反而調頭扶植了立訊精密和緯創。而華為則找到了比亞迪這個完美的planB,富士康落得個竹籃打水一場空。
庫克到訪立訊精密
更別提今年那場“媽祖托夢”的鬧劇。
好在,郭臺銘及時剎車,在前不久高調表態力挺華為,支持國產芯片研發。
一步踏錯、一場黃粱。2020年,富士康業績4連降已成必然。這在郭臺銘46年的戎馬生涯中,還屬首次。
09 十年
10年前,郭臺銘因“13連跳”闖進公眾視線,人們突然發現有一個龐然大物叫富士康,那里被描繪成地獄般的“血汗工廠”。
10年前,任正非開啟終端戰略,華為手機誕生,卻因卡頓、發熱、閃退惡評不斷。任正非一怒之下,親手砸了樣機。
遭遇滑鐵盧的華為Ascend D1
10年前,美國《時代》周刊年度人物評選,“中國工人”位居次席。評語中寫道:
中國帶領世界走向復蘇,首先要歸功于千千萬萬個勤勞堅韌的中國工人…
《時代》周刊給中國工人的配圖,來自深圳某光電科技公司
10年后的今天,華為深圳總部夜夜通明,無數工程師正咬牙向科技的皇冠——芯片發起沖擊。
而千里外的鄭州富士康航空廠區,白天蕭索如鬼城,夜晚則是煙火人間。
鄭州富士康周邊的夜晚
25萬人在這里來來去去,他們用枯燥至極的重復勞動和毫無尊嚴的生活,在過去30年扛起中國制造之名。
悲壯又殘酷。
如今,我們又來到了十年的節點,見證中國制造新的征程。
華為說:
除了勝利,我們已經無路可走。
因為只有勝利,才能讓中國升級,我們的產業工人才不用重復昨天的故事。